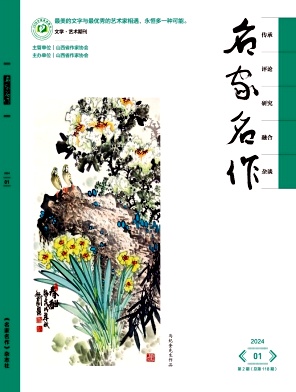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非叙事性话语
[摘 要] 作为话语模式的一个范畴,非叙事性话语常与作品的叙述者及其背后的隐含作者有着密切联系。在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大量采用非叙事性话语“侵入”文本,用议论性话语表明叙述情态,用自由间接性引语揭示人物心理,用介绍性文字填补叙事空白。非叙事性话语虽然游离于情节之外,却是叙事性文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展现了叙述者的主观判断和价值立场,又反作用于文本,体现了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自由性和先锋性。
[关 键 词] 王安忆;《长恨歌》;非叙事性话语;叙述者;话语模式
引言话语分为叙事性话语和非叙事性话语,而非叙事性话语主要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借用叙述者的声音与读者直接对话,并建构叙述行为的真实。[1]胡亚敏对非叙事性话语的定义是:“叙述者(或叙述者通过事件、人物和环境)对故事的理解和评价,又称评论。它表达的是叙述者的意识和倾向。”[2]这一表述着重强调了叙述者在非叙事性话语中的作用。但邵宁认为将非叙事性话语简化为叙述者的评价的看法仍有待商榷,并在其论文中下了一个新的定义:“非叙事性话语是叙事学‘话语’范畴中的,由叙述者发出,表达叙述者情感态度、思想倾向、价值观念的,与叙事作品中故事情节的发展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言语。”[3]这一定义首先指出非叙事性话语仍属于话语范畴;其次强调了其与叙述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最后点明其与叙事性话语的区别,即游离于情节之外。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哪种定义,都突出了非叙事性话语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叙述者的意识、倾向和声音。小说《长恨歌》在开头就用四章描写了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迟迟不展开情节,颇似散文,可以视为典型的非叙事性话语。此外,整部小说以转述的方式讲述“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命历程,并在故事进展中时不时插入叙述者的声音,通过议论性话语表明叙述者的情感、态度;通过插入自由间接性引语揭示人物心理,显示王琦瑶复杂的心理路程;最后又通过各种介绍性文字填补了叙事空白。
一、议论性话语表明叙述情态布斯将“议论”界定为由“允许自己不但显示而且讲述的叙述者”[4]发出。非叙事性话语包含公开的评论和隐蔽的评论,其中议论、描写、说明都属于公开评论的领域,但三者在表现作用上也有区别。托尔斯泰曾说:“福音书里的‘不要议论’一语在艺术中是十分正确的:你叙述、描写,可不要议论。”[5]但与说明性和描写性文字相比,议论性话语更能直接传达出叙述者及其背后作者的情感态度,对接受者理解人物、情节具有强烈的干预性。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贯穿着各种议论性话语,从而使叙述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如在第一章第三节描写闺阁时:“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6]整个一节描写的都是上海弄堂里“王琦瑶们”的闺阁,“天真”一词意有所指,表面是在形容闺阁,实际却是指闺阁中的少女,她们本是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稚嫩可爱的,却能在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而这样的现象却非一时一刻,而是具有永恒性,生生不灭。同样,“幻觉”一词也体现了叙述者的别有用心,闺阁是幻觉,闺阁女儿渴望的金钱名利、荣华富贵、身份地位等才是真正的幻象,但“王琦瑶们”却都在做着这样的幻梦,“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这些议论性话语与中心情节并无直接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客观的轨道,却凸显了叙述者的声音。一方面表现出对“闺阁”的熟悉和了解,带有叙述者的个人感受;另一方面表现出对“闺阁儿女”的无奈和怜悯,她们出身弄堂,却在各自的闺阁中做着不切实际的幻梦,想要凭借自身的风姿改变命运,跻身于弄堂(以上为31页)之上。而这样的现象却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是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在此处,看似是对闺阁的描写,实际已经有意脱离了原有的客观描摹的轨道,仿佛把闺阁活化了,一方面把它作为人和欲望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借助分析的外壳来表现叙述者的情感、态度和评价。小说中最难遮蔽的便是叙述者的声音,只要有叙述行为,便能窥见叙述者的踪迹。而小说《长恨歌》中大量出现的议论性话语,虽然游离于情节之外,但从总体来看,却凸显了叙事者的叙述情态,能够帮助接收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领悟主题,或是起到旁观见证的作用。
二、自由间接性引语揭示人物心理按照事件在作品中呈现的方式,热奈特认为可将话语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讲述式话语”[7]。其中,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还有个“自由间接性引语”,它既具有直接引语的直接性与准确性,又具有间接引语的自由性与简洁性。同时,自由间接引语与叙述者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既能保留叙事者的声音,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表达人物话语。王安忆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指出:“一定要把小说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区别开来。”“我以前写人物对话,总是‘他说……’‘她说……’照录不误,现在,这种写法我总是力求加以避免。”“归根结底,小说语言是一种叙述语言,也可以说是语言的语言或抽象性的语言。”[8]不难发现,在小说《长恨歌》中,并未采用传统的××说“我……”的直接引语句式,而是利用自由间接性引语来转述人物对话,以叙事者的立场来代替人物发声,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小说《长恨歌》中,虽然王琦瑶爱慕虚荣、精明算计,但她的形象却并不令人厌恶,反而引发人们对她命运的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小说中大量采用自由间接引语来揭示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如,当王琦瑶获得了导演的青睐,第一次去片场拍戏时,坐在化妆室里,“她感到非常尴尬,迫切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并且,她还有些神经质地以为那位化妆师同样急于结束,因为她手的动作显得很粗鲁和急躁”。此处,叙事者与故事的主人公几乎融为一体,虽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她”,却可视为第一人称“我”的心理活动。在这一转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琦瑶内心的纠结、紧张和矛盾。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弄堂的闺阁女子,尽管她有野心、有欲望,也聪明且精于算计,但不可否认的是她还仅是个十多岁的女孩。当她第一次站在人生的转折路口时,仍不免对未知的将来有着各种担心和害怕。她既希望能够牢牢抓住这次试戏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又对自己缺乏信心,她在这突如其来的机会面前犹豫了,不知自己到底该如何选择。同时,她仿佛意识到了她即将走上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所以她的难堪背后是传统道德观念的敲击。此刻,在欲望和道德的交锋中,道德暂时占据上风,因此她恨不得这一切赶快结束。于是,自己内心的心理活动便投射到了化妆师身上,觉得化妆师也是在轻看她,也迫不及待地想结束工作。除了主要人物王琦瑶外,在对其他人物如康明逊、萨沙、程先生、蒋丽莉、严师母等的描写中,也都未采用直接性引语,而是经过叙事者的转述和过滤,由其娓娓道来。在各种自由间接性引语中,叙事者与人物融为一体,以一种非聚焦性的视角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增进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三、介绍性话语填补叙事空白英伽登将文本中未直接呈现而有待读者进行填补的部分称为“空白点”,并指出“在常规阅读中,尽管空白在作品中无所不在,但它往往被读者忽视或无意识地自动填补”[9]。这些空白点主要具有以下两个作用:首先,它能充分调动读者的参与性和想象性,读者会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去猜测、预设、填补其中的情节。其次,它彰显了叙事者主体选择的自由,于有限的篇幅中蕴含着无限的意蕴。另外,有的空白却破坏了情节的连续性,对读者阅读文本造成阻碍。而各种解释性文字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们的功能在于满足读者的这种期待,肯定虚构的再现或摹仿的倾向”[10]。解释可以是对事件做补充,也可以是对主旨、关联性或某故事要素之意义的公开说明。在《叙事学》中,胡亚敏将解释性话语分为介绍、分析、修正三个方面,而其中主要是介绍性话语。其最初主要出现在话剧作品中,舞台表现对时间、地点和情节等的限制使人物的身份、背景等内容在表演过程中难以被详细地交代,为了使观众更好地看懂剧作,便需要借助旁白来进行说明介绍。在小说《长恨歌》中同样也存在着多种介绍性文字,主要有对地区风貌、人物身份等的介绍,从而将老上海最真实可感、琐屑生动的部分细致地展现出来。
(一)对地区风貌的介绍《长恨歌》一开篇就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上海形形色色的弄堂,如石库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和一堵墙上”。新式里弄堂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弄堂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以上为32页)而不同的弄堂却代表了不同的阶级:石库门弄堂是最普遍的建筑,其居住者主要是市民阶级,王琦瑶就生活在这样的弄堂中;新式里弄堂的通风采光更好,较之石库门弄堂的生活环境更佳,居住在此的主要是家底殷实的人,吴佩珍的家就在此处;公寓式里弄堂的居住环境优雅,是一般上海市民难以企及的,主要位于上海的西区,服务的都是达官贵人,蒋丽莉就出身于这个弄堂。这些形形色色的弄堂居住着各式各样的上海市民,他们遍布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也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的“芯子”。这一部分的介绍性文字看似与情节关联不大,但从中可以窥见叙事者的情感态度,即对上海里弄和日常生活的喜爱。
(二)对人物身份的介绍《长恨歌》中有好几节都是以人物名字命名的,如“程先生”“李主任”等,这些人物都与王琦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突然出场时,就会先对其身份、家庭、背景等进行介绍。在对王琦瑶的介绍中,首句便指出她是“弄堂的女儿”,点明了她的阶级身份——上海普通的市民阶层。接着,介绍了她所住之处的状况:流言四起,老妈子与人有私情,地板下面常有老鼠出没,父亲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些大段大段的介绍性文字为王琦瑶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同时读者从这些非叙事性话语中便可推断出王琦瑶宁愿做一场繁花梦的原因,而这在文中并未直接出现。若她甘愿做一个家常的女子,又只能像她的母亲一样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她想到的从来不是波澜不惊,而是轰轰烈烈。弄堂女儿的身份局限了她的视野,使她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同时,对人物身份的介绍性文字还填补了对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空白,让人物形象更加丰富,使读者对人物的判断更加客观全面。如对康明逊身份的介绍:“康明逊是二房所生的孩子,却是他家唯一的男孩,是家庭的正宗代表,所以他不得不在大房与二房之间来回周旋。”他是一个庶出的孩子,却又不得不承担家族的责任,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大户人家的少爷,这样的出身决定了他没有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利。这样的环境造成了他软弱无能的性格,因此他只能对王琦瑶说“我无能为力”“我无可奈何”,或是以沉默来做出回应。也许,读者在阅读时对这一人物形象往往是“怒其不争”,认为他是一个负心汉。但是,当叙事者加入与其相关的介绍性文字后,使读者对他有了份同情、无奈和怜惜。这些非叙事性话语其实是在代人物发言,小说中很少涉及对康明逊内心活动的描写,所以对其身份背景的介绍也就很好地填补了因人物不善言语而留下的空白。此外,由于整部小说主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非聚焦视角,在对人物进行介绍时还常常与生动的描写和议论性的话语相结合,如“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再如“她们没有创造发明的才能,也没有独立自由的个性,但她们是勤恳老实,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常常是一边进行介绍,一边发出评论,或多或少都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态度。结束语从创作的出发点来看,王安忆创作《长恨歌》有表现个人感受的强烈需求,她想要写出她记忆中的上海,并在怀旧的浪潮中还原一个真实可感的上海。因此,她在作品中大量采用非叙事性话语,利用叙事者的发声来实现她的这一创作倾向。这些非叙事性话语不仅承担了与读者进行对话的功能,也彰显着叙事者及其背后作者的价值立场、思想情感和主体意识。无论王安忆是否有此出发点,但不可否认,在这部小说中非叙事性话语对读者的阅读体悟有着强烈的影响和干预。这种随意、大量的介入,表现出作者对叙述权力的把控,也反映出王安忆创作中的个性。
参考文献:
[1][美]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7.
[2]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3.
[3]邵宁.林白小说中的非叙事性话语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23:9.
[4][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74.
[5]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706.
[6]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Genette,G.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03.[8]王安忆,陈思和,郜元宝,等.当前文学创作中的“轻”与“重”:文学对话录[J].当代作家评论,1993(5):14-23. [9]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陈燕谷,晓未,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235.[10][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3.作者简介:徐虹(2001—),女,汉族,四川泸县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 上一篇: 对古筝演奏技巧发展的多维思考
- 下一篇: 最浅又最深的河流